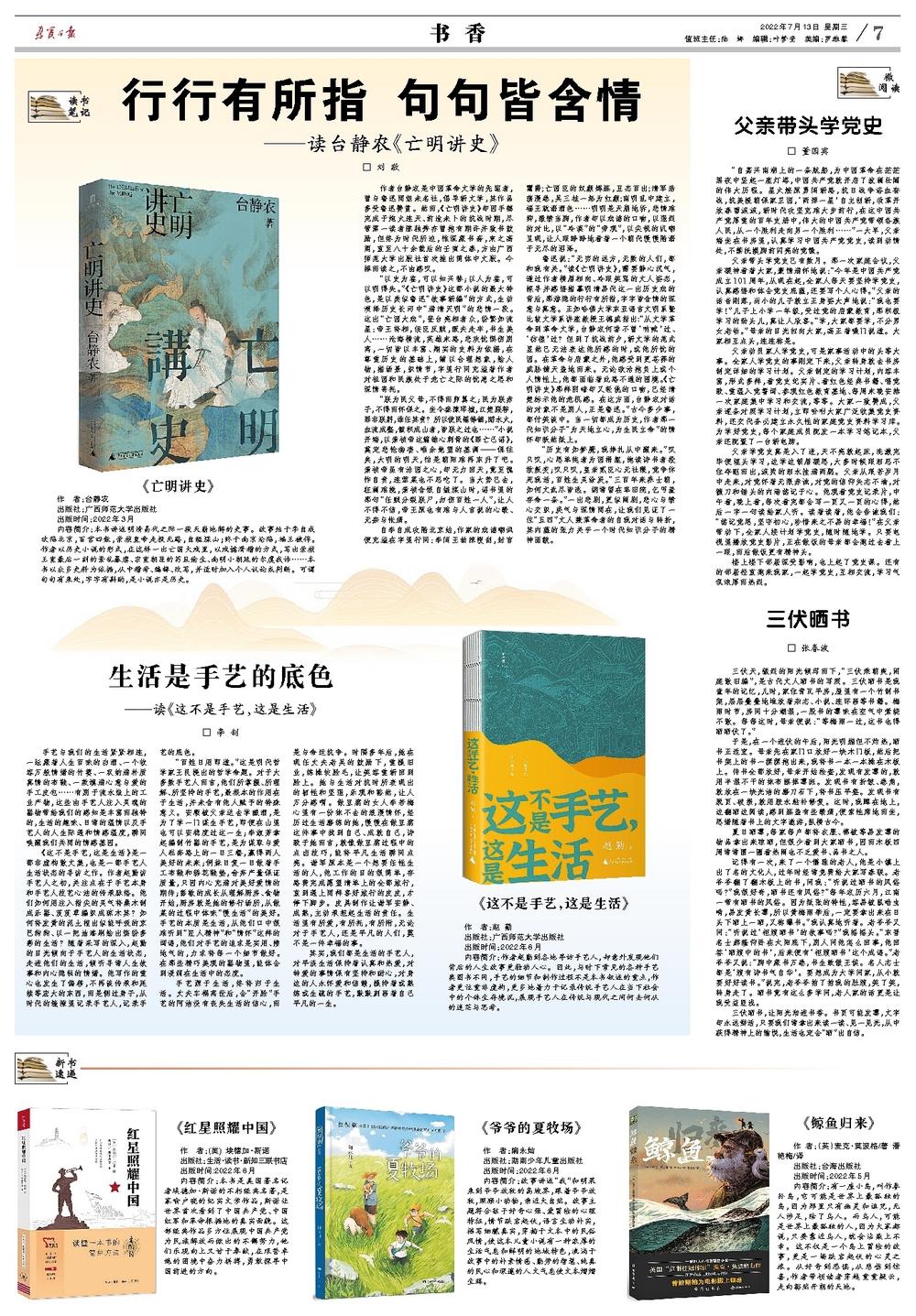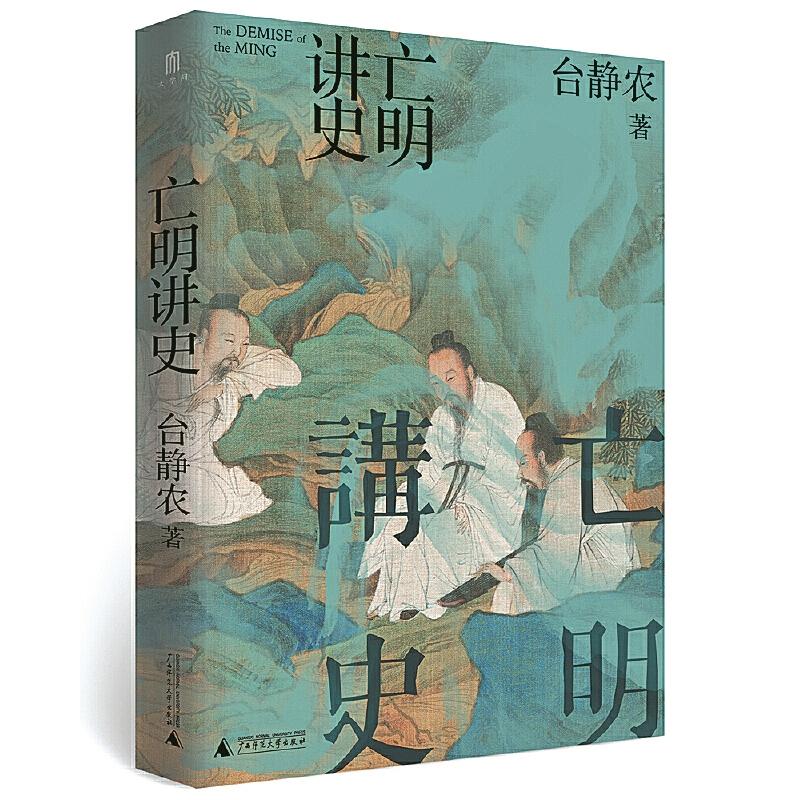作者台静农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曾与鲁迅同组未名社,倡导新文学,其作品多受鲁迅赞赏。然而,《亡明讲史》却因手稿完成于炮火连天、前途未卜的抗战时期,尽管第一读者陈独秀亦曾抱有期许并致书鼓励,但终为时代所迫,惟深藏书斋,束之高阁,直至八十余载后的壬寅之春,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今捧而读之,不由感叹。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亡明讲史》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是以类似鲁迅“故事新编”的方式,生动演绎历史长河中“满清灭明”的悲情一段。这出“亡国大戏”,登台亮相者众,纷繁如流星:帝王将相,佞臣反贼,贩夫走卒,书生美人……沧海横流,英雄末路,悲欢忧惧伤别离,一切皆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辅以合理想象,绘人物,描场景,织情节,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对祖国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忧患之思和深情寄托。
“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小说开端,以崇祯帝这篇锥心刺骨的《罪亡己诏》,奠定悲怆幽凄、唯余绝望的基调——俱往矣,大明的明天,怕是朝阳难再东升了吧。崇祯帝虽有治国之心,却无力回天,竟至愧怍自责,连荤菜也不忍吃了。当大势已去,狂澜难挽,崇祯含恨自缢煤山时,诏书里的那句“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让人不得不信,帝王原也有难与人言说的心酸、无奈与怅痛。
自李自成攻陷北京始,作家的戏谑嘲讽便充溢在字里行间:李闯王劫掠搜刮,封官鬻爵;亡国臣的奴颜婢膝,丑态百出;清军浩荡漫卷,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南明乱中建立,福王耽溺酒色……明明是天崩地坼,悲情难抑,激愤当胸,作者却以戏谑的口吻,以强烈的对比,以“冷漠”的“旁观”,以尖锐的讥嘲呈现,让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朝代慢慢陷溺于无尽的沼泽。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读《亡明讲史》,需要静心沉气,透过作者横眉相向、冷眼笑骂的文人姿态,探寻并感悟描摹明清易代这一出历史戏的背后,那潜隐的行行有所指,字字皆含情的深意与真意。正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指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静农何尝不曾‘呐喊’过、‘彷徨’过?但到了抗战前夕,新文学的范式显然已无法表达他所感的时,或他所忧的国。在革命与启蒙之外,他感受到更苍莽的威胁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政治抱负上或个人情性上,他都面临着此路不通的困境。《亡明讲史》那样阴暗却又轻佻的口吻,已经清楚标示他的危机感。在这方面,台静农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鲁迅。”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当一切都成为历史,作者那一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却跃然纸上。
“历史有如梦魇,我挣扎从中醒来。”叹只叹,心思单纯者为国捐躯,饱读诗书者投敌叛变;叹只叹,皇亲贰臣心无社稷,党争你死我活,百姓生灵涂炭。“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一出悲剧,更似闹剧,悲心与愤心交织,戾气与深情同在,让我们见证了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其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亡明讲史》
作 者:台静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明清易代之际一段天崩地解的史事。故事始于李自成攻陷北京,百官四散,崇祯皇帝走投无路,自缢煤山;终于南京沦陷,福王被俘。作者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在这样一出亡国大戏里,以戏谑滑稽的方式,写出崇祯王室最后一刻的紊乱暴虐、宗室朝臣的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的尔虞我诈……本书以众多史料为依据,从中稽考、编辑、改写,并适时加入个人议论或判断。可谓句句有来处,字字有斟酌,是小说亦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