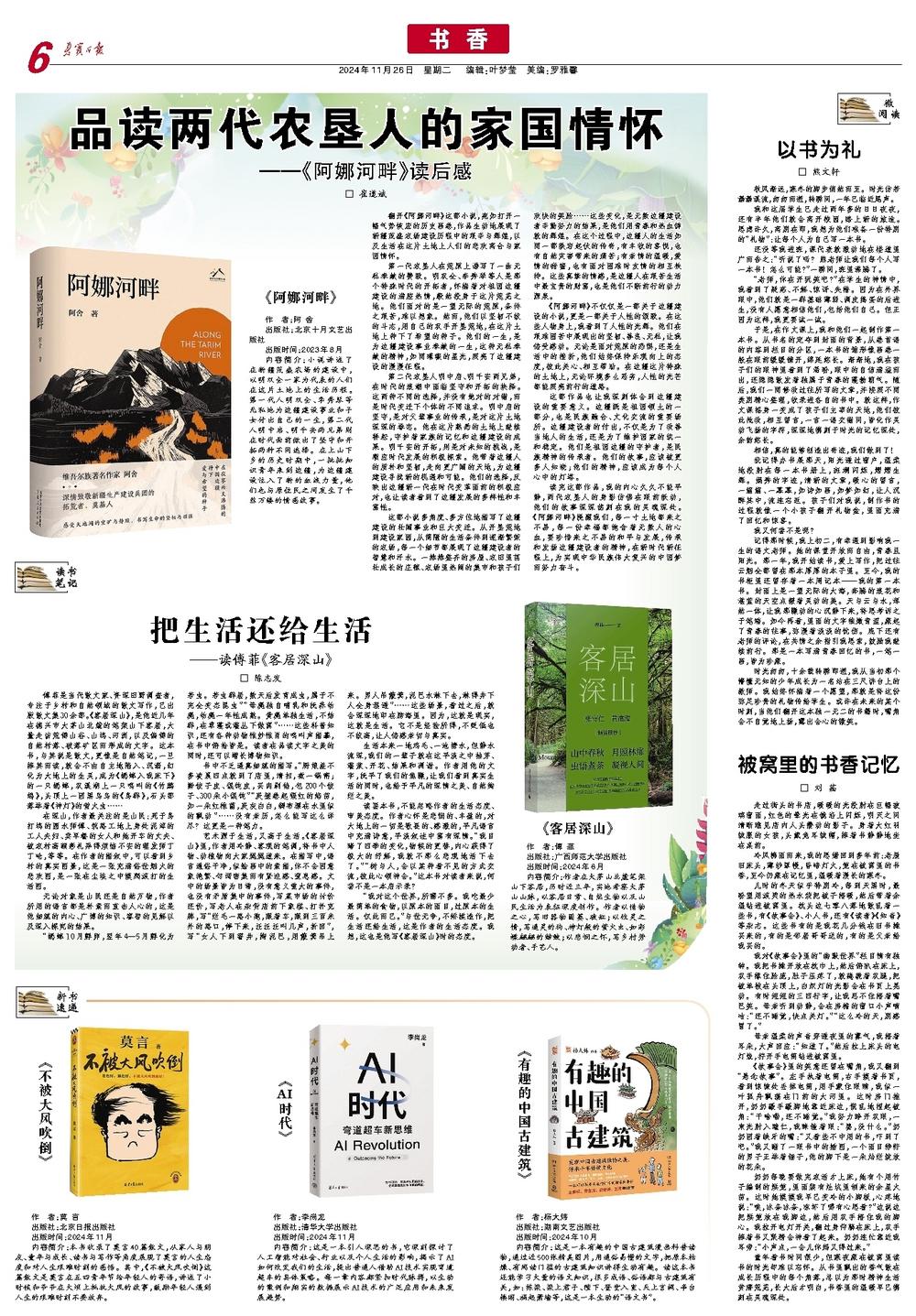傅菲是当代散文家、资深田野调查者,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已出版散文集30余部。《客居深山》,是他近几年在德兴市大茅山北麓的笔架山下客居,大量走访荒僻山谷、山坞、河洲,以及偏僻的自然村落、破落矿区而形成的文字。这本书,与其说是散文,更像是自然笔记,一旦捧其而读,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溺,幻化为大地上的生灵,成为《蟋蟀入我床下》的一只蟋蟀,双溪湖上一只鸣叫的《竹鹧鸪》,头顶上一团黑乌乌的《鸟群》,石头部落举着《神灯》的萤火虫……
在深山,作者最关注的是山民:死于鸟打坞的圆水师傅、筑路工地上身处泥淖的工人夫妇、卖早餐的女人和她开车的丈夫、被农村高额彩礼弄得烦恼不安的理发师丁丁呛,等等。在作者的描叙中,可以看到乡村的真实图景,这是一张充满俗世烟火的悲欢图,是一张在尘埃之中摸爬滚打的生活图。
无论对象是山民还是自然万物,作者所用的语言都是朴素而直击人心的,这是他细腻的内心、广博的知识、睿智的见解以及深入探究的结果。
“蟋蟀10月孵卵,翌年4—5月孵化为若虫。若虫群居,数天后发育成虫,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母麂独自哺乳和抚养幼麂,幼麂一年性成熟。黄麂单独生活,不结群,在草蓬或灌丛下做窝”……这些科普知识,还有各种动物惟妙惟肖的鸣叫声描摹,在书中俯拾皆是。读者在品读文字之美的同时,还可以增长博物知识。
书中不乏逼真细腻的描写。“厨娘差不多凌晨四点就到了店里,清扫,煮一锅粥;擀饺子皮、馄饨皮,买肉剁馅,包200个饺子、300朵小馄饨”“炭壁卷起猩红的焰苗,如一朵红椎菌,炭灰白白,绸布漂在水里似的飘动”……没有亲历,怎么能写这么详尽?这更是一种笔力。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客居深山》里,作者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将书中人物、动植物向大家娓娓道来。在描写中,语言通俗干净,似绘画中的素描,你不会因意象艳繁、句词密集而有紧迫感、窒息感。文中的场景皆为日常,没有意义重大的事件,也没有矛盾集中的事件,写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写老人在杂货店前下象棋、打扑克牌,写“烂毛一路小跑,跟着车,跟到三百米外的路口,停下来,汪汪汪叫几声,折回”,写“女人下到窨井,掏泥巴,用簸箕吊上来。男人吊簸箕,泥巴水淋下去,淋得井下人全身湿透”……这些场景,看过之后,就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因为,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它不是经验所得,不贬低也不拔高,让人倍感亲切与真实。
生活本来一地鸡毛、一池塘水,但静水流深,我们的一辈子就在这平淡之中抽芽、灌浆、开花、结果和凋谢。作者用他的文字,抚平了我们的焦躁,让我们看到真实生活的同时,也给予平凡的深情之美、自然绚烂之美。
读罢本书,不能忽略作者的生活态度、审美态度。作者心怀是悲悯的、丰盈的,对大地上的一切是敬畏的、感激的,平凡语言中充满诗意,平淡叙述中富有深情。“我目睹了四季的变化,物候的更替,内心获得了极大的纾解,我就不那么悲观地活下去了。”“树与人,会以某种看不见的方式交流,彼此心领神会。”这本书对读者来说,何尝不是一本启示录?
“我对这个世界,所需不多。我吃最少最简单的食物,以原本的面目,过原本的生活。仅此而已。”与世无争,不矫揉造作,把生活还给生活,这是作者的生活态度。我想,这也是他写《客居深山》时的态度。